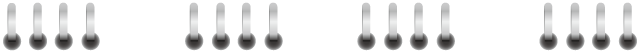

因为连住两晚,我们在达来呼布镇过的就是完整一天,行动起来没那么急促了,甚至还带几份懒洋洋般的悠闲。秋日晴朗的下午时分,郊外额济纳河边很多卖哈密瓜的农用小卡,吸引我们靠了过去。




这些卖瓜人并非二道贩子,而是自产自销的当地瓜农。很有意思,他们卖瓜都不带秤,论个头出手,只分两档:大的一律10元/只,小的5元/只。如此,有些块头较大的起码突破20斤,划下来每斤仅5毛钱。我想判断这比在镇江能便宜多少,却对家里的行情又一无所知。
就在刚才,往返策克口岸途中,我们不断看见两侧硕果累累的哈密瓜种植地。“哈密”是新疆的地理标识,但“哈密瓜”并不只新疆独有,同处大西北的甘肃敦煌及内蒙古阿拉善盟一带均为产地。我们在镇江吃哈密瓜的时候只顾着吃瓜了,根本不会去烦神它产自哪儿,或者想都不用想地认为必是新疆土特产。所以,过去我们究竟有没有吃过内蒙古的哈密瓜,这还是个谜。
一路上,这种价廉物美的时令甜品,我们可没少吃。甚到吃得过于奢侈,我经常看到林庆生这片还没啃上几口,就又重换一片。倒是想说说他,可欲言又止:因为事实上如果不像他这样子吃的话,造成的浪费极有可能更大。

卖哈密瓜的摊点,达来呼布城里城处随处可见,其中,在额济纳河沿岸相对形成聚集。原因很简单,瓜跟着人走。一水横陈、苍黄萧然的额济纳河边,是众多游客驻足观光、拍摄休闲的风水宝地,几乎成为不设门票的抢手景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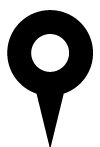
地球某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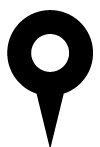
地球某处


我们当然不会漠视这么好玩的地方,也在河边疯了老
半天。老田的大机子有一阵子没掏出来了,此刻兴致甚浓,再度进入紧张而严肃的创作状态之中。冷不丁,林庆生连招呼都不打,就一把从他手上夺走了相机,然后东瞅瞅西转转,忽立忽蹲,到处按快门。
艺术的力量是会这样让人失控的。面对天地间如此之壮美,庆生心中无疑也产生了表达的冲动。不过,写剧本还行,摄影并不是他的强项。事后据老田披露,当时庆生并没在他相机里留下太多能拿得上台面的作品,大部分都删了,有几张甚至完全是朝天放枪,画面上一滴水也没挨着。身为市影视家协会副主席的林庆生,天生十足文艺范,他那堪称顶级的摄创造型却是令人过目不忘。
上图:老田在分析视角
下图:林庆生对额济纳河的表达

有不少游客,是在额济纳河边支起帐蓬,露营过夜。分析这存在多种可能:要么没订到酒店旅馆房间;要么就是主动选择这一体验方式。


前面说过,虽没刻意搜寻,但我们还是四处顺带张罗着在额济纳旗有没有来自江苏的老乡车子。当天下午河边消闲的时候,真就撞上了,而且在这块自驾车扎堆的地方,同时发现两辆:一辆来自南京,一辆来自无锡。连同先前在巴彦浩特的那辆“苏L”,内蒙境内我们一共遇到三辆江苏老乡。
来自无锡的这辆自驾车,是一对年轻父母携带着娇小可爱的女儿。简单交流中得知,差不多同一起点上“穿过大半个中国”来额济纳看胡杨,其倒“U”型线路与我们正好相反:他们是经河西走廊由酒泉进来,下一步将由贺兰山出内蒙、入宁夏。
举家三口,心无旁骛、自由自在地走遍中国,这份快乐、浪漫与意义,我想应是甚于我们朋友间的结伴而行。


若是以孤立的世俗眼光看,额济纳河真可谓貌不惊人,河水浑浊,河面亦不宽敞,没有惊涛骇浪,且由秋入冬时节,它还在一天天消瘦下去。然而,正是这条不可貌相的河流,却蓄满话不尽的自然与人文,蓄满历史传奇。

如同扬子江是长江的一个段落名称,额济纳河则是黑河的一段。发源于祁连山脉的黑河,为中国第二大内陆河,全长800余公里,在流入内蒙境内之前,已恩泽青海、甘肃两省。
唐诗人王维在额济纳地界上所写《使至塞上》,其中两句“大漠孤火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千百年来脍炙人口。对“长河”,目前有两种未成定论的考证说法:一是指黄河,一是指额济纳河(黑河)。此刻算我有点偏心吧,我当然更倾向于后者。
一地皆有一地的母亲河。多重意义上的文脉,最终可归结为一水之系。失去水,新疆的楼兰古城就毁了;
因为额济纳河改道,境内西夏及元、繁盛一时的边防要塞——黑水城,亦渐而没落。如果失去额济纳河,额济纳的数十万亩胡杨必将无家可归。但是,我们期愿这个假设永远不要兑现。
奔流不息的额济纳河,见证了远古的纷纭世事,更见证了历经4代人、跨越74年,抒写清朝年代悲壮之歌的土尔扈特万里东归。其中,由阿拉布珠尔率领的最早一支东归先遣部队500余人,斗志斗勇,吃尽千辛万苦,终于回到祖国,被清政府优待安置在额济纳一带肥美的草原上。不久,额济纳正式建“旗”。

额济纳河的水滋养着美丽的胡杨、广博的草原,也滋养了一代代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各族同胞。著名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便是土生土长的额济纳旗人。她的一曲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,既唱给所有的草原,更是唱给额济纳。(未完待续)
作者:王景曙
编辑:吴悠


















